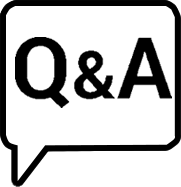| 對於患上晚期癌病,我多次提到要尊重病人的意願。 但若遇上早期癌病,而病人的意願卻是放棄医治時 … 55歲,女性,証實患上早期大腸癌,但兩年多來一直不肯醫治。 外科同事轉介給我們,看看有無他法。 「醫生,對於這種病,我的經驗多的是。 我知道這種病怎樣醫也不會醫好的,你不用勸我了。」 她肯定地說。 「是誰告訴你的? 早期腸癌經手術後的生存機會高於七成!」 我說。 「你是騙不了我的。 我是負責院舍服務的,我照顧的院友皆是經西醫治療後半死不生的。 橫豎要死,我才不要死得這麽辛苦 …」 我真是被她氣得哭笑不得。 「無法醫治的癌病病人才需要院舍服務,你整天在院舍工作,當然看不到醫好了病的另一羣啊! 我有很多醫好了十多年仍在覆診的相熟病人,我叫他們跟你談談好嗎?」我說. 「我家中有兩位成員都是長期病患,經手術一做,變成兩個植物人。 我必需留下我這條命,因為現在家中就只剩下我可以照顧他們。 若手術不成功,又多一位半植物人,家中又會多一個負累 …」她仍是肯定地答. 我有點動氣了。 「既然你知道你的家人這麽需要妳,妳更應盡早把病醫好,留下健康的体魄去照顧他们。 再拖下去,妳會变成末期病患者,到時由誰來照顧你们一家三口?」 這句似乎奏效,她沉默了一會,但維持不了兩分鍾,她又變回原來的她。 最後,她連臨床心理學家也不肯見便走了。 不過,已經兩年了,她可能已錯過了醫病最關鍵的時刻了,而她所執着的悲劇也一步一步變成真實了。 個人的執着真的可以使信念成真。 當人帶着偏見看事物,往往像自我催眠般,一開始便架構起一個悲劇的劇本,日常生活對自己的執念相反的會視而不見,卻只接受與劇情相乎的人和事,最可怕的是,這些人和事會加強當事人的信念,使 他/她 漸漸地成為劇中的主角,直至結局出現,以悲劇收場 … 佛家宣揚的放下執念,談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