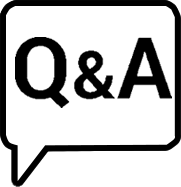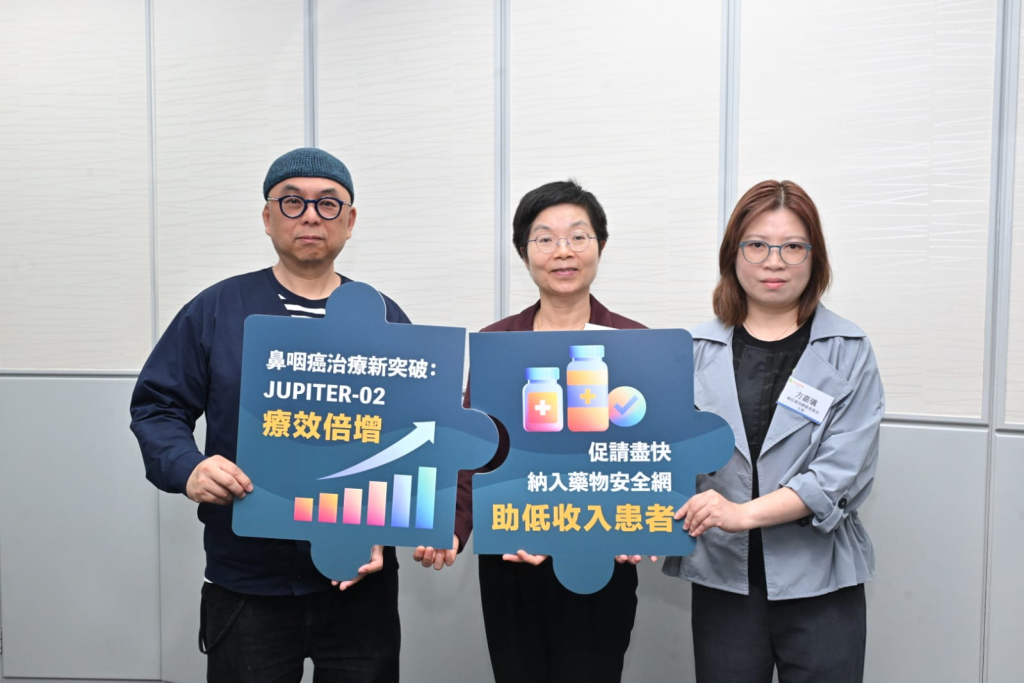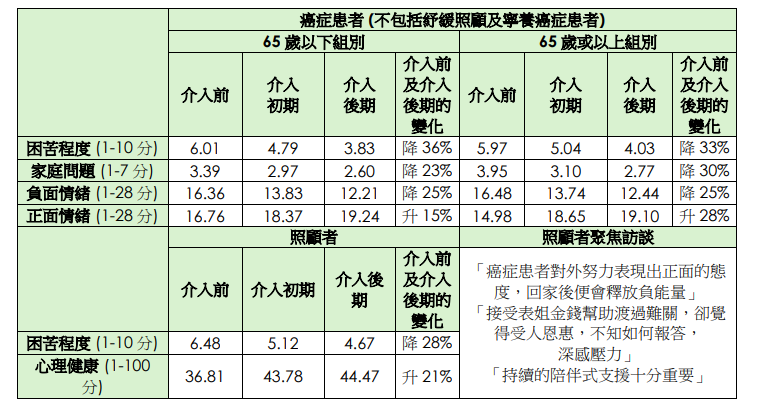• 多達六成已購買醫療保險的受訪者表示,對持續上升的醫療保費感到憂慮,反映 出大多數人對現有醫療保障的信心不足
• 73%擁有住院現金保障的受訪者認為保障年期應延伸至最少 75 歲,另有 42% 表示住院現金計劃應提供終身保障,反映住院現金保障年期存在明顯缺口
• 保誠推出全新「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為市場首創 1結合終身健康 及人壽保障與資金增長機會的住院現金計劃,為客戶健康和財富雙重護航
(香港,2025 年 7 月 10 日)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保誠」)今日公佈全新「住院保障調 查」2(「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對應付醫療開支缺乏信心,尤其在面對慢性疾病所 帶來的財務負擔方面更感壓力沉重。即使已購買醫療保險,受訪者仍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負擔, 而住院現金保障的缺口亦相當明顯,反映市場對更全面,並能有效紓緩財務壓力的長遠醫療保 障計劃有迫切需求。

大眾對醫療開支信心不足 受保人士對保障範圍存有憂慮
調查指出,隨著醫療開支持續上升,68%受訪者表示會主要依靠醫療或住院保險應對相關費 用,65%依賴個人儲蓄,46%則選擇公共醫療作為保障。然而,僅 36%受訪者有信心透過 以上方式應付突發醫療開支。隨著年齡增長,信心程度進一步下降,在 51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 中,只有不足三成(29%)對此表示有信心。
即使已購買醫療保險的受訪者,亦面臨不同程度的財務壓力。調查顯示,多達六成受訪者表示 對持續上升的醫療保費感到憂慮;44%則憂慮若未提出索償,所繳保費將被浪費;40%表示 擔心現有醫療保險未能充分涵蓋醫療開支,尤其是康復相關費用(如物理治療或中醫)。上述 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對現有醫療保障的信心不足,對保障範圍及實際效益存有憂慮。
調查亦發現,慢性疾病所衍生的開支進一步加劇大眾的財務壓力。66%受訪者對慢性疾病的 治療、住院及其他醫療費用感到憂慮,其次為相關長期照護費用(65%),及患病對家庭成 員的影響(60%)。此結果反映慢性疾病不僅對個人健康構成挑戰,更對家庭經濟造成長遠 影響,成為醫療保障規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1 以上有關此計劃為「市場首創」提供終身健康及人壽保障與資金增長機會的住院現金計劃的描述,是基於我們截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對香港主要人壽保險公司發售予個人客戶,並提供每日住院現金保障的住院現金基本計劃之現有市場資訊的理解及解讀
2 保誠於 2025 年 6 月以網上問卷形式,對 336 名 18 歲或以上的現有客戶進行調查,其中包括香港及中國内地受訪者
住院現金保障存明顯缺口 長期保障方案需求殷切
當市民無論因輕重傷病需要住院時,住院現金能靈活為各項醫療開支(包括復康,護理等)提 供現金支援。然而,調查結果顯示此類保障在市場上的滲透率仍然偏低,僅 29%受訪者表示 擁有住院現金計劃,遠低於擁有危疾保險(64%)和儲蓄人壽計劃(61%)的受訪者比例。 由此可見,市民對住院現金保障的認知仍有待提升。
此外,在已擁有住院現金計劃的受訪者中,73%認為保障年期應延伸至最少 75 歲,亦有 42%認為相關計劃應提供終身保障,反映現時住院現金保障年期明顯不足,進一步顯示市場 對更長期住院現金方案的需求殷切。
調查亦指出,七成擁有住院現金計劃的受訪者每日可獲得的住院現金金額低於港幣$1,200 元, 僅有 21%認為現有金額足以應付實際需要。此結果反映市民對住院現金保障的保障水平有更 高期望,盼能獲得更切合實際需要的的保障方案。
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結合健康與財富保障
保誠保險首席產品管理總監馮偉成表示:「透過是次調查,我們觀察到市民在長遠醫療保障方 面普遍準備不足,不少人僅擁有基本醫療保障,可能面對較多保障限制(例如自付額等),或 在復康保障方面亦顯不足。即使已購買醫療保險的受訪者,亦可能因保費持續上升,或未曾提 出索償而擔心所繳保費被浪費。有見及此,保誠推出全新『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 旨在讓客戶以限期供款,便能同時享有終身健康及人壽保障,以及長期財富增長,協助客戶在 守護健康的同時,建立更穩健的財務基礎,靈活應對未來不同階段的醫療及財務需要。」
「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為市場首創 1,提供終生健康及人壽保障與資金增長機會 的住院現金計劃。計劃涵蓋每日住院現金保障,並就長期住院、嚴重腦退化症、柏金遜病,以 及市場首創3的嚴重糖尿病,提供一筆過賠償。計劃同時設有隨時間增長的保證現金價值及非 保證終期紅利,讓客戶即使未曾提出索償,亦可於在生時透過計劃累積資金,於身故後傳承財 富。
「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以短至五年的保費,提供終身保障,產品特點*包括:

3 以上有關此計劃就嚴重糖尿病提供一筆過保障為「市場首創」的描述,是指受保人在確診嚴重第二型糖尿病且毋須出現糖尿病 併發症的情況下提供一筆過保障。這是我們基於截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對香港主要人壽保險公司發售予個人客戶並在受保人確 診個別疾病時提供一筆過賠償的基本計劃之現有市場資訊的理解及解讀
4 「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為美元保單產品,港元金額乃根據假設匯率 1 美元兌 8 港元計算,實際匯率可能會有所變 動
保誠首席客務營運及健康保障業務總監歐陽佩玲表示:「保誠一直用心聆聽客戶所需,致力成 為客戶健康之旅的守護者。透過推出『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我們希望全面回應 客戶對長遠保障的需求,協助紓緩因患病而帶來的財務壓力,讓他們安心專注康復。計劃亦設 有專屬核保指引,讓患有常見病況的客戶可獲得更周全保障。未來,保誠將繼續履行於客戶最 需要時伸出援手給予支援的承諾,透過更貼心和全面的健康保障方案,全方位滿足客戶的多元 化需求。」 *如欲了解有關「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之詳情、相關條款及細則,請瀏覽保誠官 方網頁之產品介紹及產品小冊子
免責聲明 「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由保誠保險有限公司承保。此文件不包含本計劃的完整條款及細則並只作參考之用。如欲了 解更多有關本計劃之其他詳情、條款及細則,請向保誠索取保單樣本以作參考。此文件僅旨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保誠在香 港境外提供、出售或遊說購買任何保險產品。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屬於違法,保誠 不會在該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出售該保險產品。
5 此專屬核保指引是基於「保誠加護一生住院現金儲蓄保險」健康保障為預支賠償,且具儲蓄成分,性質有別於其他實報實銷或 住院現金健康產品
6 疾病需並非因該身體部份的結節/腫瘤或其他已存在疾病直接或間接引起,公司將需視乎醫療文件,包括病理報告,作最終理賠 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