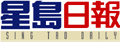新加坡‧研究另一常規療法‧細胞治療醫治血癌
(新加坡23日訊)患有急性和慢性髓細胞白血病的血癌病患,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選擇細胞治療作為其中一種常規療法,減少體內因化療、放射療法或骨髓移植產生的毒素,提高治療的安全性。* j; X: ]- y) M
tvb now,tvbnow,bttvb,tv series,tv drama,movie,bt,download z: h+ t! T$ S2 p
所謂細胞治療(cell therapy),指的是把從血液中抽取的細胞,經過科研人員約2至6個星期的培育、改良和強化後,注入癌症患者體內,以攻克癌細胞。
/ f# P O3 D) D/ _
過去5年來,細胞治療受到醫學界廣泛關注,並取得快速進展,但較為醫療界認可的治療範圍仍屬血癌。tvb now,tvbnow,bttvb,tv series,tv drama,movie,bt,download9 a* n. 7 Z% W0 c& Z7 M) R
7 s+ B1 p! d6 u8 V2 {8 R1 t
減少毒素公仔箱論壇8 M5 1 O1 M* p( n
提高骨髓移植效果tvb now,tvbnow,bttvb,tv series,tv drama,movie,bt,download9 Y# L4 Z: w8 V) v; ]( j6 u
本地科研人員目前研究的,則是一種被稱為細胞因子誘殺細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簡稱CIK)的特殊免疫細胞。
tvb now,tvbnow,bttvb,tv series,tv drama,movie,bt,download6 Z$ ?% {- E% }, B& o
衛生科學局血液服務司醫療總監許文才醫生受訪時指出,骨髓移植是增加高風險血癌患者存活率的一種治療法,但病患康復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骨髓本身,而是因為骨髓中產生的CIK細胞,這也引發了醫療界對細胞治療的關注。
1 _# o# D+ X$ x/ y- h
他說:“由於骨髓並非來自病患本身,外來細胞在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攻擊正常細胞組織,因此可能出現排斥反應和毒素。tvb now,tvbnow,bttvb,tv series,tv drama,movie,bt,download, d2 c1 `* G- F& ^
“我們希望繼續研究如何改良細胞,找出能抵抗血癌的好細胞,讓它們發揮最大的功能,丟掉壞細胞,幫助改善骨髓移植的效果。”
化療放射治療
會產生毒素, F& x5 @& b6 e
另外,化療和放射治療是癌症患者的傳統治療法,雖然很多病患因此好轉,但治療藥物中仍含有毒素。
許文才強調,細胞治療目前無法代替骨髓移植或化療,只能作為輔助療法,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減少其他療法所產生的毒素,或消除化療後仍存留的癌細胞。
衛生科學局自2007年起與新加坡中央醫院合作,針對48名年齡介於20歲至70歲的急性和慢性髓細胞白血病(myeloid leukaemia)病患進行臨床試驗。6 ?7 |6 l9 N( O N. j6 v8 G
未來可成常規治療法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2 ~9 u) Y, N z9 ?/ @' E+ S
目前,試驗已接近尾聲,並在國外醫學雜誌上發表了試驗成果,預計可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常規治療法。公仔箱論壇+ f7 l1 @) k# L9 @( X. Q. d
許文才透露,患者的康復過程非常順利,只有少數出現發燒等症狀。
公仔箱論壇* C" c+ d% l8 o6 L
48名患者中,有28名病患用的是自身的細胞,另20名病患用的則是由別人捐贈的細胞。
細胞治療將成未來趨勢公仔箱論壇& F- }+ D4 k2 M) Z:
許文才指出,細胞治療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未來10年研究範圍將逐步從癌症擴大到細胞的重造功能,如幫助中風病人重造受損的神經細胞。公仔箱論壇& r: {# }. o, 3 h1 D
他說:“很多疾病都因感染而起,但病患大多都靠會引發副作用的類固醇控制感染。科研人員發現人體中有部份細胞能減少感染,但目前還在非常初步的研究階段,我們希望在兩年內看到成果。”* } W$ w; g5 s" P) t6 ~
此外,從明年1月起,當局也將與新加坡臍帶血庫合作進行臨床試驗,研究臍帶血細胞對急性血癌的治療效果。
(星洲日報/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