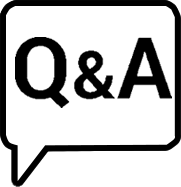城中活動
2024-07-20 12:00 上午
CICF x K&K Charity – 逆風計劃 -「 敢動人生2024 計劃 」🌞 帆船篇
2024-07-16 4:00 下午
CICF x K&K Charity – 逆風計劃 -「 敢動人生2024 計劃 」🌞 – 地壺球
2024-06-12 10:00 上午
留住這一刻 ——維港帆船體驗慈善計劃
疑難排解
我們有一群專業的醫護人員及相關朋友,隨時解答大家的疑難,立即提交疑問!
會員註冊
成為會員,可以第一時間接收由病患者和照顧者角度出發的資訊,立即行動!
或許你會想看
【癌症檢查】甲狀腺有癌指數嗎?| 黎逸玲醫生
如何測出甲狀腺癌 時常有病人問我:有沒有癌指數可以測出甲狀腺癌? 我的回答是: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先說簡 […]
無用|黃曉恩醫生
向患上癌症的病友和家人解釋過治療方案後,很多都會問道:「醫生,這個治療會不會『無用』呢?」將心比己,這實在是一 […]
當下的妙|黃曉恩醫生
有說:「當對音樂的熱愛到達一個程度,就不會甘於只做聽眾,卻渴望上台演出。」這實在是作為業餘音樂愛好者如我的寫照 […]
蝴蝶|黃曉恩醫生
我是腫瘤科醫生,她是乳癌病人。我卻不是她的醫生:我們兩年前在「恩典同行小組」──瑪麗醫院癌症病友關懷小組裡遇上 […]
港九新界一日遊|黃曉恩醫生
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的臨床醫生大多都是駐診於一間醫院:主要的工作都在這裡進行,只是間中需要到其他醫院看診或開會。 […]
輕輕的她走了|黃曉恩醫生
「唉!我快要死了!」她嬌嗔道。 四十出頭的她是我的新病人。一年多前她確診第四期乳癌,轉移到肝臟和骨骼,在公立醫 […]
腦中的練習|黃曉恩醫生
小時候,敬愛的鋼琴老師大概不忍我因為資質平庸而灰心,對我不厭其煩地循循善誘:令鋼琴技術進步的不二法門就是不斷練 […]
醫生掉眼淚|黃曉恩醫生
你別管我骨子裡是樂觀還是悲觀(或許我自己都說不清),反正我喜歡逗人樂,面對我的腫瘤科病人亦然。我明白罹癌絕對不 […]
這麼近,那麼遠|黃曉恩醫生
她都累得不想動了。 她是遺傳基因BRCA1的攜帶者:這基因在她家族裏一代一代流傳下去,帶有的女仕一生中達八成多 […]
寫作的二月|黃曉恩醫生
二月,我的寫作季節。 兩年前的二月,我首先成為了「博客」,正式踏上寫作路!那陣子我遇上數位「知識型」的癌友和家 […]
隔空|黃曉恩醫生
疫情期間,許多平常覺得理所當然的群聚活動都需要改成線上進行,有人歡喜有人愁。 使用各種軟件,就可以方便地上課和 […]
認識你|黃曉恩醫生
認識你,最初是工作上的一個機會。在那次訪談中,你的專業與我的醫學共舞。我納悶:何以對答中的你對各種深奧複雜的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