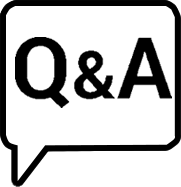城中活動
2025-08-24 2:30 下午
「癌症病人北上就醫」講座
2025-08-16 2:30 下午
Coloring your life 肺癌治療分享 x 土耳其水拓畫工作坊
2025-08-09 2:30 下午
毋忘愛 x 癌症資訊網 |告別練習社(第二場)
疑難排解
我們有一群專業的醫護人員及相關朋友,隨時解答大家的疑難,立即提交疑問!
會員註冊
成為會員,可以第一時間接收由病患者和照顧者角度出發的資訊,立即行動!
或許你會想看
【有誰共鳴】 嘉賓:余思遠醫生
心胸肺外科專科醫生余思遠最近在商業電台節目《有誰共鳴》中分享了他的故事。他揭示了學醫背後那段孤獨而又艱辛的旅程 […]
【有誰共鳴】 嘉賓:Christine Fok
Christine 發現患有四期胰臟癌時,未有即時向相依為命的爸爸道明一切。爸爸看見她日漸消瘦,她也辯稱自己減 […]
【有誰共鳴】 嘉賓:黎逸玲醫生
《有誰共鳴》節目有外科專科醫生黎逸玲醫生同大家分享行醫二三事。 有些人會覺得醫生每日面對生死,可能早已沒甚感覺 […]
【有誰共鳴】 嘉賓:音樂治療師 Hugo
音樂治療師 Hugo 細細個嘅時候,並唔係大家想像咁鍾意音樂。後來有一年喺英國讀書,開始摸索自己喜歡嘅音樂⋯⋯ […]
【justwannasay】獻給所有受癌症影響的每一位
這是屬於我們的旅程 不知不覺中,突然就開展了與癌症共舞的訓練人生。 漸漸發現原來我的天賦之一就是 […]
戰勝食管癌,聽聽多學科專家怎麼說!
2025年1月25日,北京時間晚上 8 時,由香港大學知識交流辦公室主辦,全球腫瘤協作(GCOG), 香港大學 […]
容許犯錯:成長的必經之路
多謝@drip_music_records 的邀請、有機會和幾位音樂達人分享我對藝術治療的一些看法,相信再多的 […]
基因檢測好有用 幫你對症下藥治療轉移性大腸癌
隨著醫學不斷發展,近年有愈來愈多新藥面世,晚期的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亦出現很大的改變,特別對腫瘤細胞進行基因檢測 […]
【腦腫瘤關注月】甚麼是腦膜瘤?|鄒淑韻醫生
甚麼是腦腫瘤? 腦部大約可分為大腦、小腦、腦幹。大腦扮演人體機能總指揮,左右兩邊各有四個組成部分,包括額葉、頂 […]
痱滋與舌癌 | 黎逸玲醫生
舌癌的可怕之處,在於舌頭是維持生活品質其中一個重要的器官。舌頭幫助我們說話構音、咀嚼、吞嚥和感受味覺。不少病人 […]
提供另類療法是無牌行醫嗎? | 黎逸玲醫生
有美容中心負責人涉嫌勸喻三位癌症病人不要向私人醫生求診和服用化療藥,又替他們進行心靈治療、磁療法和回春療法,收 […]
【渣打香港馬拉松2025】醫患陪你跑-黃韻婷博士
🏃🏻個人簡介 Dr Wendy 黃韻婷博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活動期望 / 心聲 忙到裙拉褲甩 […]